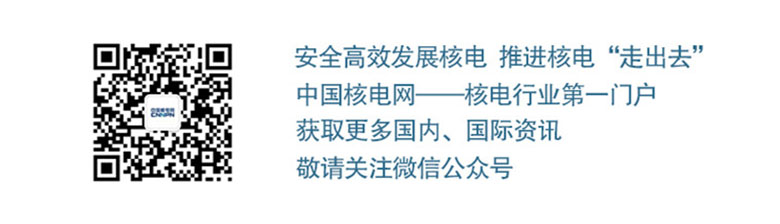在众多的核工业功勋人物和院士中,王乃彦的人生经历好像特别丰富。他的命运轨迹,一次次被机遇和自己改写。
所有他经历的人和事,在他讲来都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——这可能并不仅仅因为他的经历本身,而在于他的性格。他在科学的理性之外,还洋溢着对世界的浪漫情怀和不断学习的激情。
他走到哪学到哪,活到老就学到老。哪怕只是生活中的细节,他在多年后都记得清楚。

偷拨时钟被发现
王乃彦的家乡是福建省福州市。他读小学的时候,福州被日本占领了,他跟着父亲退到了沙县,在沙县师范附属小学读书。
学校安在一座破庙里,把菩萨请走,就成了教室。风吹起来庙里漏风,到冬天的时候很冷。黑板,是从锅炉里弄点烟灰和胶拌在一起,涂在刨平的木头上。庙里没地方活动,老师就带他们去沙堤和河滩,在外面做各种游戏。
只有两位老师:一位是校长,教数学;还有一位是校长夫人,教音乐。就在这里,王乃彦说自己“受到了很好的教育”。
王乃彦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。校长拿一个马蹄钟让他负责打下课钟,其实就是用一个铁块儿去敲。
到冬天,年纪大的学生就教王乃彦“使坏”,叫他早一点把钟往前拨,提前下课去晒太阳。晒太阳的时候又把钟给拨回来。
老是这么干,校长就觉得不对头。有一次上课,王乃彦正偷偷拨那个钟,一下子就被校长看见了。
下课的时候,校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,摸摸他的头跟他说:“小孩子一定要诚实,不能搞欺骗的事啊。”这是他关于诚信的第一课。
挂红花、骑大马的梦没成
王乃彦读完小学,抗日战争已经胜利。他回到福州,上了福州市第一中学。
1949年8月7日福建省福州市解放,王乃彦在1950年5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也就是现在共青团的前身。同年7月,他被送去参加了福建省团员干部训练班。
这个训练班里大部分是北京、上海来的革命青年,他们随军南下,穿着新四军的灰色军装,王乃彦“羡慕得不得了”,就向他们要一套。因为他年纪小,给了他一套最小号的。他觉得非常神气,一直穿到上北大。后来到大学不穿了,他就拿去海淀的一家裁缝店改成了衣服的内衬。
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,号召青年学生参军,从训练班回来的王乃彦立刻报了名。他很激动:“只要上面一批准,胸口挂一个大红花,骑上大马就走了。”
没想到命令下来,所有报名参军的同学一律改为参加土地改革。

王乃彦给学生们授课
“政工干部并不缺乏,科学人才是国家急需的”
到了农村,“老农才厉害,不规则的土地绕着走一圈,报出来是5分,量出来就是5分左右。”王乃彦跟着学,到后来报出来的结果也八九不离十。
除了帮农民分土地,王乃彦还帮他们修水利。土改工作干了1年零2个月,他被评为福州土改工作一等功臣。年纪小、工作出色,当时缺乏年轻知识人才的福州市委就注意到了他,希望他能到市委去工作,给领导当秘书。
王乃彦对这个选择不无动心,就向自己所在工作组的组长孙作青征求意见。
孙作青说:“你来自知识分子的家庭,毛主席已经提出了‘向科学进军’的口号。政工干部,我们军队里面多得很,并不缺乏,但是将来要去攻克科学堡垒的人,才是国家急需的。”
这番诚恳的话,直接决定了王乃彦的选择,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
123456789全做
王乃彦在土改结束后回到省一中,因为已经1年多没上课,学校说他必须补考才能接着上学。
利用中午时间,数学和物理老师轮流给王乃彦“开小灶”补课。因为他好学,老师们乐意帮王乃彦补课。老师说习题做1357,他都是123456789全做。
等补考完了,班主任告诉他,成绩还是名列前茅。
正要进入高三,又有了第二次参军机会。王乃彦梦想重燃。但这一次也没走成,王乃彦在第一关身体检查时就被刷下来了。因为他太瘦了,体重都没超过50公斤。
就这样,王乃彦下定决心考大学。1952年,他与同班的5个同学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。
转入“北大六组”
在北大物理系学完基础课后,第3年要分专业。王乃彦最喜欢无线电电子学。这源自他跟高中物理老师林童雀学过组装单管矿石收音机。
王乃彦一心一意准备搞无线电电子学,还买了好多书,却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折——他被调到了原子能专业。
当时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,所以从六所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生集中到北大学习,成立了“北大六组”。
“‘北大六组’其实也在北大里,和我原来的同学就隔一条街,但不能告诉同学我到什么地方去了,和家里也不能讲。”学习的课程都是保密的,笔记本和教材都是发的,笔记本上还印有编号。
1956年,王乃彦从“北大六组”毕业,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的钱三强小组。

钱三强(右二)王乃彦(右三)与众人合影
钱大师指点
在钱三强的领导下,王乃彦开始用中子飞行时间法研究中子能谱。当时苏联援助建了一个反应堆,他就在那上面研究。
大学刚毕业的王乃彦,很幸运地到了这个先进的项目里接受训练,并得到大师的指点。“我那时候喜欢理论,对实验不太重视。钱先生听我做报告后,鼓励我要钻研理论,也要重视实验。”王乃彦说。
1959年,他做出了一批中子能谱的参数,和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表的参数基本一致。这是中国发表的第一批中子核数据。
钱三强很满意,叫王乃彦填表,准备把他送到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去。
“我选的人就是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”
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当时是社会主义阵营联合的一个研究所,中国出了25%的钱。中国第一批派去的工作人员有王淦昌、周光召等十几人,主要是研究高能物理和理论物理领域。对方希望也能派中子物理方面的人去,钱三强就想到了王乃彦。
没想到申请书发过去不久,却被退回来了。对方表示:希望你们至少派一个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过来。
但钱三强又把王乃彦的材料给寄回去了,并且告诉对方,他选的人就是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的人!

王乃彦辅导学生
“等他回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”
到了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,王淦昌陪王乃彦去见了实验室主任弗朗克院士——也就是一开始拒绝他申请的人。
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举行成员国全球代表会时,钱三强来了,会后提出要参观中子物理实验室。弗朗克就让王乃彦在中子100米飞行站上等着。
钱三强看到了王乃彦,就问弗朗克:“王在你这儿工作,你满意不满意?”
弗朗克答道:“王工作得很好,今年年初刚获实验室的一个奖,我和他的组长都很满意。至于他到底怎么样,等他回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“并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”
王乃彦说,弗朗克是个真正的学者。作为院士、诺贝尔奖获得者,他还经常到实验室去查看记录实验的笔记本,看完以后会问些问题。
弗朗克一到实验室,王乃彦一下子就站起来,弗朗克说:“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尊敬,但是年轻人,并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。我如果都听我老师的话,我的诺贝尔奖就得不到了。”
后来王乃彦出去做报告,总是说他有两个老师,一个王淦昌,一个弗朗克。
后来中苏关系破裂,中国退出了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,王乃彦也就回国了。在杜布纳度过的这6年,对他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。

王乃彦与家人合影
结婚都不是自己去领的证
王乃彦和爱人结婚时,因为他在短期回国学习班学习没法请假,不能亲自去领证。他爱人随便找了一个同学去办了结婚手续。
1965年回国后,王乃彦被分配到了九院,去了青海金银滩基地,他非常高兴。当时王乃彦有了一个女儿,但正好妻子也要去山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两口子都不在家,就把女儿送去中联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寄养。
青海是边区,王乃彦的工资翻了一倍,吃饭基本不要钱。王乃彦就把工资的一大半寄给了这个中联部的同志:“我在青海要那么多钱没有用,不用买很多东西。”
这个朋友很疼爱王乃彦的女儿,但有一次骑自行车带她的时候,小女孩把脚搁了进去,整个脚背被车轮的钢丝绞住了。王乃彦得知后非常揪心。
他出差回来看女儿,“我女儿管中联部这个同志叫爸爸,管我倒叫叔叔。”直到王乃彦的妻子从山西回来,才把女儿领回身边来带。

王淦昌(左)与王乃彦(右)合影
“要知道为什么成功,为什么失败”
在青海草原,王乃彦听理论部的邓稼先、于敏讲氢弹的理论模型。而他要思考怎样在实验场上做热试验,并通过试验证明它可行。
王乃彦和同事准备了试验方案,向理论部汇报。邓稼先、于敏对他们提出要求:“老王,如果实验成功,那是皆大欢喜。但是成功了,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成功;退一步想,如果实验失败了,也要知道为什么失败。”
院领导说:“你要什么条件,只要中国有,我都给你搞。”王乃彦他们压力很大:“万一实验失败了,却什么原因都找不到,那还得了?!所以我们真的是拼命干。”
1966年12月,即将开始中国氢弹原理试验。冬天的戈壁滩,冰天雪地,一讲话胡子就结霜,眼镜片都模糊了。在核爆塔上完成准备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后,王乃彦和同事把窗户擦干净,涂上防霜油,最后一批从塔上下来。
起爆后,地动山摇,试验成功了。但是为什么成功?必须拿数据来说话。
王乃彦等7个人需到距离爆心500米、1000米、1500米处去拿胶卷。但因为刚爆完放射性剂量太大,暂时不允许进去。
1967年的元旦,王乃彦与同事们就住在帐篷里,天天打电话,问指挥部是否可以进去回收胶卷,担心再不回收的话胶卷就毁了。指挥部一直说不行。
过了大概10天,指挥部说可以进去了。王乃彦他们高兴极了,没有考虑个人安危,立即准备进去。
他们是第三梯队。第一梯队是防化兵,第二梯队是工兵,沿路测量放射性,设置警戒线。“工兵进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处在警戒线上,看到工号门前的沙袋全都被吹得一塌糊涂,铁门被冲击波压得整个变形了。”解放军拿着铁锹把铁门给撬开。“他们吃了很多剂量,因为打先锋的都是他们。”
门开了,王乃彦他们往里冲。7个人分乘两辆吉普车,冲击波冲得土路都是坑坑洼洼的。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往里冲,以减少受辐照的剂量。
冲到洞口,再冲进暗室,暗室里虽没有光,但他们之前都经过训练,在黑暗中可以非常熟练地把胶卷从照相机里面取下来,塞在铅罐里面,用最快的速度跑出来。
他们拿到的试验结果,不仅证明了当量比原来理论设计的要大,而且知道了原因。王乃彦在北京向理论部汇报,汇报完以后于敏特别高兴,握着他的手说:“老王啊,做这个实验的时候,我心里还有点害怕。现在我心里终于踏实了。”
“英语怎么算过关?就是要随便讲什么都可以”
王乃彦被选为院士以后,不久又被派去参加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选举。
当上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后,王乃彦重新开始学习英语。“要接待外宾了,就想我要跟他聊什么,要用的词语都准备好,结果根本不行。英语怎么算过关?就是要随便讲什么都可以。你老跟人家说客套的话,根本建立不起感情。”
60多岁的王乃彦,买了磁带和教材,每天抽出5个小时学英语:他早上5点半起来学1个小时,上下班来回近1个小时,中午休息有1个小时,晚上9点前把所有的活动都结束,再学到11~12点。家里放着大大小小很多的收音机,他“走到哪儿学到哪儿”。
两年后,王乃彦从副理事长升为理事长,用英文发表就职演说。讲完了,全场掌声如雷。从台上下去后,秘书长麦克(美国人)拥抱他说:“王,我不知道你还有外交才能!”
原标题:《曾经想“挂红花、骑大马”,后来却被调到钱大师的“北大六组”》
作者:核芯报道工作室 李春平
来源:中国核工业
免责声明:本网转载自合作媒体、机构或其他网站的信息,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,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。本网所有信息仅供参考,不做交易和服务的根据。本网内容如有侵权或其它问题请及时告之,本网将及时修改或删除。凡以任何方式登录本网站或直接、间接使用本网站资料者,视为自愿接受本网站声明的约束。